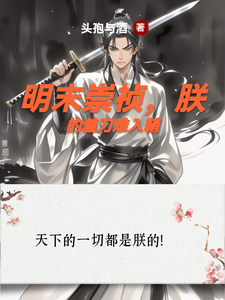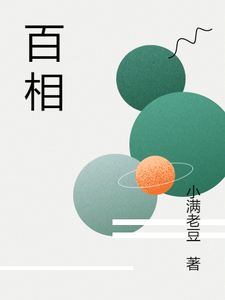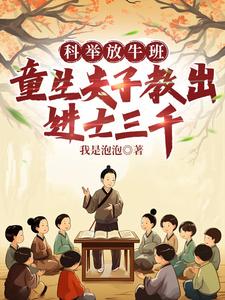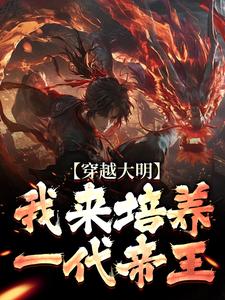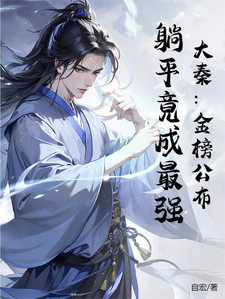明末崇祯,朕的羞刀难入鞘朱由检希凌雪番外+结局(头孢与酒)剧情介绍_明末崇祯,朕的羞刀难入鞘精彩试读
一、故事梗概
1627年10月,18岁的朱由检穿越成为刚登基的崇祯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处于小冰河期,粮食减产、田地荒废,地方官员盘剥百姓,朝堂上东林党等官员贪腐,九边军镇将官腐败、吃空饷,商人氏族倒卖军需资助外敌。他意识到若不改变,自己将重蹈煤山自缢的命运。幸运的是,他触发了【大明借贷】系统,可先贷后偿,初始信用等级LV1,可支配白银一百万两,借贷周期三十天。他了解到逾期还款将被关闭系统权限且会死亡,所以决定利用系统改善大明的状况。
朝堂上,面对宣府军镇的军饷催要,户部尚书称国库存银不足六十万两,而半个月前奏疏上还记录有五百三十万两。皇帝质问时,官员们各怀心思。朱由检让大臣们捐钱,只有魏忠贤和王承恩拿出真金白银,其他官员大多用俸禄充数。东林党人周延儒提出削减卫所、拆撤驿站、缩减厂卫编制的建议,实则对魏忠贤宣战,钱谦益附议并提出加两成民税,朱由检愤怒地对钱谦益施以杖刑并最终将其斩杀,以警告群臣不要打百姓主意。
之后皇帝决定让英国公带兵押送一百万两银饷(来自系统的内帑库)去宣府军镇,一是解决军饷问题,二是整顿边镇。同时他免除农人赋税,打算主收商业税,以收拢民心、稳定局势。退朝后,他去内承运库监督银两交接,成功提前还款提升了信用等级和授信额度,虽尝试卡BUG失败,但仍利用系统资金安排英国公押送三百万两白银去宣府和辽东军镇。他还召秦良玉入京,视英国公、秦良玉、满桂为王牌,准备依靠厂卫和这些人来稳固皇权、整顿京营腐败。
夜晚,朱由检召见魏忠贤和锦衣卫指挥使田尔耕,对他们进行敲打和试探,打算继续重用魏忠贤,让他整顿内务府,让田尔耕派手下监视公卿大臣的不法行为。最后周皇后前来御书房,送人参羹关心皇帝,皇帝向皇后诉说自己虽有抱负但面临诸多困境。
二、内容解答
问题1:朱由检穿越成崇祯皇帝后,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答案:大明王朝内忧外患,内有粮食产量锐减、官员腐败、百姓生活困苦,外有后金和蒙古的威胁,同时国库空虚,难以维持九边军镇的军饷等庞大开支。
问题2:【大明借贷】系统对朱由检有什么重要意义?答案:系统可让他先贷后偿,在初期就有一定的资金可支配,如一百万两白银,这有助于他解决军饷等紧急问题,提升信用等级后还能解锁更多额度,是他改善大明状况的重要助力。
问题3:为什么朱由检不杀魏忠贤?答案:因为魏忠贤能为皇帝筹钱,且在抗击外族问题上立场坚定,相比文官集团,他更能维护皇权,是现阶段朱由检可用之人。
问题4:朱由检斩杀钱谦益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答案:钱谦益提出加两成民税来解决边军军饷问题,而朱由检不想剥削百姓,希望通过惩治贪腐、加商税来解决财政问题,钱谦益的提议触怒了他。
问题5:朱由检免除农人赋税的目的是什么?答案:一是收拢民心,让被压迫的农民看到希望,减少农民起义的可能性;二是根据实际情况,明末农民生活困苦,继续征税也难以榨取油水,不如调动农民耕种积极性。
问题6:朱由检为什么要重用英国公、秦良玉和满桂?答案:英国公忠诚且能执行皇帝的命令去镇抚军镇,秦良玉是巾帼女将,她的白杆兵能威慑外敌,且她曾拿出自家资产充作军饷勤王,满桂是保卫京师力战阵亡的将领,这三人都有助于朱由检整顿军事、稳固政权。
问题7:朱由检召见魏忠贤和田尔耕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对他们进行敲打和试探,想要瓦解东厂和锦衣卫之间的利益关系,让他们为自己效力,比如让田尔耕监视公卿大臣,让魏忠贤整顿内务府。
三、小说点评
这篇小说情节丰富且紧凑。故事背景设定在明末这个动荡的时期,通过主角朱由检穿越成为崇祯皇帝,展现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局面。人物塑造方面,主角朱由检有现代思维又努力融入皇帝角色,他的果断、睿智以及对百姓的关心都表现得很生动。魏忠贤等历史人物形象也被重新解读,突破了传统认知。小说中的朝堂斗争描写精彩,各方势力的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如东林党与魏忠贤之间的矛盾,大臣们面对军饷问题的不同表现等,都让故事充满了张力。同时,系统元素的加入为故事增添了独特的趣味性,使传统的历史穿越题材有了新的看点。在叙事上,流畅自然,将历史事件、人物关系和主角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吸引读者深入阅读。
四:《明末崇祯,朕的羞刀难入鞘》朱由检希凌雪精彩内容:
张家从成祖时期,受爵英国公。
一直到大明崇祯末年,世袭罔替,代代忠良,为大明抛头颅洒热血,马革裹尸、沥血疆场。
他的忠毋庸置疑。
但是其他国公,就有点走歪了。
有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的。
有蜷缩封地,富甲一方,祸害乡里的。
更可恶的是还有投降建奴的。
除此之外,朝堂上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投降派。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锦衣卫里那个叫骆养性的家伙。
他吃里扒外,跟东林党蛇鼠一窝。
都是暗通建奴,乞首投降的墙头草。
综合比较下来,历史上被文人污抹的比炭都黑的魏忠贤居然还成了最大的忠臣。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之所以变得优秀,全靠同行衬托。
朱由检重用魏忠贤也是无奈之举,纯属是一群矮子里面拔高个。
虽然魏忠贤身背二十四桩大罪,但是架不住他聪明。
他很清楚自己权倾朝野的仰仗是谁给的。
他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于皇帝。
所以他是朝中少有的积极维护皇权的人。
在忠诚方面,魏忠贤用生命上了一课。
后世他倒台的时候,明明可以网罗天下爪牙铤而走险,却选择了自尽谢罪。
这样的人,能奸到哪儿去?
有时候朱由检也不得不感慨,大明的阉人们属实是真豪杰。
浙、楚包括东林党,那才叫伪君子。
因此,朱由检不但不会裁撤厂卫,还会强化东西厂跟锦衣卫的权力。
如今的大明,虽然得了大病,却也没有到了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的地步。
大明需要刮骨疗伤。
他这位皇帝就必须得下猛药、出重刀!
掌控厂卫,让他们大肆盘查。
一旦查实贪赃枉法,那就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主打一个管杀不管埋的心态。
至于什么杀了官员,谁来给朝廷办事?
这样的言论对于朱由检来说,就是杞人忧天。
笑话,古往今来不知道有多少身怀真才实干的有志之士想要做官而没有门路。
朝廷之中那些个腐朽的官位,不知道会被多少人争的头破血流呢。
还怕没人做官?
当年开国皇帝朱元璋监斩洪武大案的罪犯,整个京师血流成河,人头滚滚。
当年明成祖朱棣照样把贪官跟方孝儒一家杀的整整齐齐。
但是朝廷的官位空缺了吗?
不但没有空缺,参官入仕者反而如同过江之鲫,前赴后继。
所以朱由检杀几个典型,简直毫无心理压力。
哪怕换一批武德充沛的丘八们上去替换掉那些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官员,也比现在的情况强。
所以,这场反腐风暴没有下限。
只是眼下迫在眉睫的是先把东厂跟锦衣卫给支棱起来。
处理掉厂卫内部的腐化,把这两把属于皇帝的刀刃磨锋利了。
除此之外,急需诰命夫人秦良玉入京护驾。
免得朱由检自己莫名其妙的死在深宫大墙之内!
在这样的基础上,以白杆兵跟英国公的所部组建精锐部队。
把大明那些悍不畏死的丘八们重用起来。
让他们跟当年打元朝一样痛打建奴。
正在朱由检心思电转之间,乾清宫门外的敬事太监曹化淳躬身小跑了进来。
“皇爷,皇后娘娘来了。”
朱由检看了一眼曹化淳,便往堂前走去。
他对曹化淳的印象不错。
曹化淳跟其同朝为官的次兄曹化雨一样,同王承恩一道属于绝对的帝党心腹。
但是曹化淳又跟魏忠贤不和。
因为魏忠贤害死曹化淳的恩人,司礼太监王安,还曾把曹化淳逐出北京城,留置到金陵待罪。
这样的关系,正好可以被朱由检利用。
等大明朝局稳定,江山永固之后,便打算借助曹化淳制衡魏忠贤。
只不过现在曹化淳还有一些污点,那就是他跟东林党交好,好在他没有什么恶迹。
但搞笑的是,他被东林党背后捅刀子。
东林党在投降清军之后,散布野史,反污曹化淳才是大明‘开城纵贼’的罪魁祸首,以此来掩饰‘东林党’被迫折木而栖的无耻之举。
“臣妾参见陛下。”
束发盘冠的周皇后朝着朱由检缓步迎上,在朱由检身前几尺处止步,欠身施礼。
“皇后免礼。”朱由检走上去牵着皇后的玉手。
周皇后年正芳华,贤女味十足,既有风韵,也有出尘不染的温婉气质。
朱由检看着皇后,脸上涌现出几分怜爱之意。
有时候他觉得崇祯皇帝是幸运的。
他遇到了一位有层次的女人,这个女人品味高洁,性情严谨,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广受人们尊敬。
历史给她的评价便是‘孝节’,很多人在她身上看到朱元璋的结发妻子‘孝慈高皇后’的影子。
最关键的是,出身清贫的周皇后从不恃宠而骄、更不会居位至傲。
晚年跟着崇祯过着缩衣减食的生活,崇祯在煤山自缢后,皇后也随之殉节。
这种情愫,如同烙在骨子里的印记,不是穿越就能斩断的。
“陛下,臣妾听闻陛下操劳国事,特意熬了人参羹,还请陛下注意龙体。”
周皇后转身示意身后丫鬟将熬好的粥放在御案上。
“皇后有心了,朕近日来确实忙的焦头烂额。”
在结发之妻面前,朱由检的语气变得柔和了许多。
“臣妾知道陛下政务繁忙,只是不知如何为陛下解忧。”周皇后言语间透着些许自责。
“朕有皇后,再忙也值得。”朱由检快言快语,拉着周皇后的手坐回到龙椅上,顺势将皇后拽到自己腿上。
“陛下,这是御书房……”周皇后羞臊的叱责了一句。
朱由检洒然轻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御书房怎么了?”
“陛下……”
“朕辛苦多日,就不能享受享受吗?”
“陛下莫急,臣妾永远是陛下的人,陛下先用膳。”皇后语气糅杂着些许严肃,严肃当中掺杂一丝丝激切。
正在她欲拒还羞的时候,朱由检一手搂着皇后,一手扶额,长长的叹了口气。
“陛下怎么了?”周皇后关切的询问。
“朕……朕徒有一腔抱负,却因囊中羞涩,以至于朕的惊世才华毫无用武之地。”
“如今九边缺饷,庶民缺粮,文官缺德,武将缺胆魄;朕深居简出,已无力支应庞大的开支,如今负债累累,心乱如麻。”
朱由检开口便是叫屈。